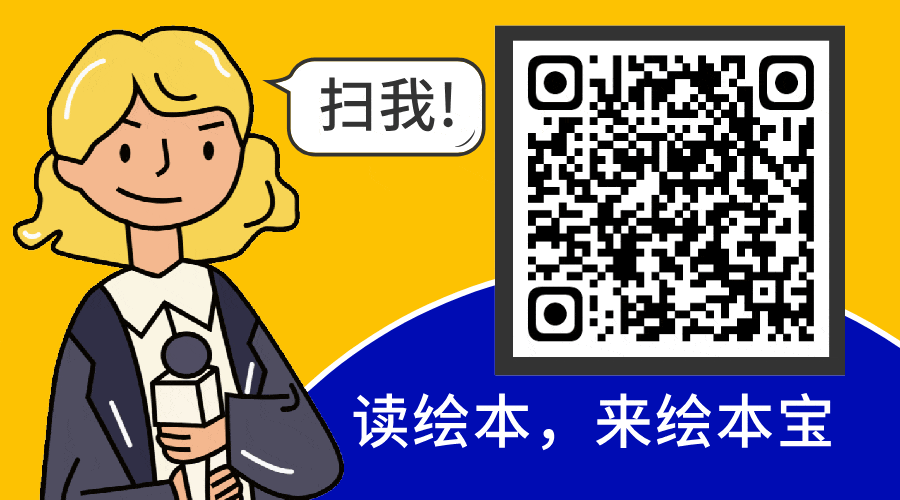

作者: 蓝鸭鸭

这是一个朋友的“述职报告”。--题记
求学的时候是最快活与最轻松无忧的时间,一生中,也许就只有那么十几年可以在其间渡过。犹记得,曾经有过那么多的理想,比如医生为病者排患疾、比如老师教书育人、比如艺术家将自己的作品显现于人……太多的美妙仿佛一个太高的起点,让我措手不及地接受大学毕业后一年的漫长等待。在我们的这个时代,已经没有什么名正言顺的“上学-毕业-工作”了,一切都走入时代的正轨。
在大学里,我是非师范院校的师范专业学生,过多地学习着书本理论,所以我平时就是不上课,考试也能拿到学期奖学金,于是有同学认为我是神。我总是用着一种不同常人的方式在学习和实践,在毕业前的实习里,带了一个初一班一个月的语文课,我从来不备课,上课不用课本,要学生先预习新课,第二天以提问的方式,让学生熟悉课本知识,把学习的自动权完全放在学生手里,结果一周下来的学生测试,居然只有五个人及格,高分率1.5%。指导教师要我仔细想想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,我无可置否,学生在短短时间内习惯不了我的教学方式,况且他们才接触初中学习?所以我相信,如果我一向担任教师工作,在教学上一定会有新的突破,因为现在提倡素质教育,而不是应试教育。但是我终不能证明自己的这种能力了,大学毕业一年后,通过竞争上岗,我走上了从政的道路,在一个小镇的计生站挂任镇所辖村之一的村主任助理,当起了名副其实的农民,走进了农民阶级。这都是在此之前,我所始料不及的,可是人生代价总得有个地方去体现,在事先无可选择的状况下,我只能走上为人民服务的道路,当起人民的公仆了。
因为分配在镇计生服务站,第一天报到就被不知谁是领导,谁是一般干部的三个女人拉下村去,他们辨别一个瘦精精、一个胖呼呼而丰满、一个头发乱糟糟走着内八字脚,那一胖一瘦看起来都挺精明的样子,那外形不大整齐的却有些让人忍俊不禁。镇里下队是出车的,坐在车上前往目的地时,她们说是去搞妇女孕、环情搜检。到了村就跟着他们瞎走,也不知哪村是哪村,只晓得走了一家又一家,一会东家,一会西家,进得有人在家的门去,就让那家的年青女子弄些干净的尿液来,然后用一种蓝白色的细长纸条插进尿液里,不一会就出现白色反应条,最终那个大内八字脚的拿出一个小红本子来写上些什么,递给那被搜检的年青女人,要她收捡好。就到下一家去了,我诧异,这就叫做妇女孕、环情搜检?边走边看着,那三个女人都叫我多学着些,以后就是我自己一个人负责了。我的嘴差点没张成O型,原来农村工作就是这样的?
那是一个占地范围比较宽广的村子,共有七零八落的八个自然村寨,将我的“战线”拉得很长。镇领导将我送下村的那天,才发现居然是第一天空上班到过的那个村子。不管怎么样,那天熟悉了几个主要的村干部,看了村里给我安排的住处,然后吃了村里热情地安排一桌酒筵,大家叫着我小崔,灌下一碗当地的土酒,结果弄得我话都不会说了,什么以后多多帮助、多多体贴、多多教育的话全跑出来。那村长一听,顿脸都拉了,我想他一定是觉得我这大学生话都说不利落,敢情是来下放劳教的。领导们酒足饭饱后,就打道回府了,说是把我交给村里了。看来我真是被下放了的知青,大学里的一切理想都要这个落后的村寨里被一点点磨灭,让我晓畅,走入生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,现实真的不等于理想。
其实下村的时间并不是许多的,隔三差五地自己出钱搭车(单位的公车是为领导安排的)到村里,转上二三个小时就算一天工作了,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镇政府里参加一些大型的资料预备工作,应付即将到来的各种搜检。直到那年的七月里下了一场大而长的暴雨,涨潮的大水把大半个镇区淹得一片汪洋。为了真实地统计灾情,我风风火火地在村长的陪同下,把整个村子在一天之内走完了,和我同样被累得气喘嘘嘘的村长直埋怨我工作没经验,却也只得跟着我满村子走。我知道他的意思是我应该坐着等,他安排村小组长去做这些统计工作。这是我第一次走完一切村寨,每一个小组,每一块田地。
村里安排的那间小屋,我一次都没有再出来过,记得第一次出来看到的那些见到人都毫无顾及出入的老鼠(mouse),总让我不寒而栗。我只是在每个季度妇检时,学着第一次下村时那三个女人的方式,给村里年青的妇女搞简朴的妇科搜检。或是到村里出出宣传栏,公开一下有关的打算生育政策或是指标。起初我到村里,是很难找到搜检对象的,之后才有村民通知我,因为不熟悉,许多人都以为我是来抓丁的(也就是把计生手术对象请去做手术)。不久过后,我和那些年青的妇女都熟悉了,谁家姓甚我谁,谁家有几个小孩,什么时候出生的,是否是打算生育手术对象等都搞得一览无余。在搜检时,也会像模像样地通过其尿液调查一些所谓的病情。同时,宣传一下有关的打算生育知识,打消未术者畏惧被“捕”的顾忌。在手术对象中,每个符合结扎手术的女人们都极度地畏惧,谁也不愿意把康健的自己送去在肚子割上那么一刀,虽然这种男女结扎手术,其实不过是将输精或输卵管捆绑或是剪断捆绑。
村子里有几个村寨是在大山的最深处的。因为早在束缚战争以前,这里办过一个矿厂,所以仅且只有一条大路可以直通山脚,再有就是山寨的终点那条顺着小溪(brook)直流而下的山间小径,直连镇政府所在地。每次我踩着碎石镶嵌的黄泥小径,浏览着一路的青山密林,走入村子最深处时,都会有种走进原始的感觉,那里的村民太过于淳朴,走在路上遇见了,他们一脸敦朴地笑着,叫我崔同志或是崔村长,于是我浑身起鸡皮,竟依然喜欢有人称我为小崔的。寨子里到处是放养的鸡和狗,山上林子里有马和牛,村民有的在地里劳作,有的在院子里忙和,有的赶着猪儿乱跑,有的带着小孙孙转来转去……一派世外田园的景象。农户们总是很热情的,有的时候还没窜完整个寨子,饭就吃好几顿了、茶 都喝好几杯了,总是不好谢绝的。有次同事打趣我,吃人不穷,胀破你狗肚。
小娥的家是我唯一没有吃过饭的一户人家。她的家在村子的最末端,其实也不是她家,是她男朋友的家。说是她男朋友,是因为她和他并没有一纸婚约,只是二个人就这样在一路了,而小娥是我工作的对象。小娥的家是一栋很老式的木石结构的二层房子,站在她家门口,看到门条上许多写着咒语式的横幅和字条,看不懂什么意思的雨字头文字,听说屋主是一个四十岁左右半道士,头发留得老长,戴着道士标志的帽子,妻子早年给他生了一女一男就跟人跑了,现在他独自摆了张床,一人住在楼,自己开火做饭,更多的时候他喜欢外出“云游”每年年关才返来。在自己大块的责任田里种粮食、种蔬菜,险些一年不愁没吃的,有可能的话还送到集市上卖掉,赚些钱。好几次我在上班的路上,看到他挑着一点点小菜,一摇三晃地在路上走着。
小娥是我们搞人口普查时清理出来的流动人口对象,那时我竟然不知道她在村里住了一年之久,按普查规定,已算是常住人口了。小娥挺着大肚子,更招摇地说明我了我的失职。于是我开始说服小娥去手术,把孩子引掉,虽然美国人常拿这个来抨击中国的人权,但我迫不得已为我的失职而弥补,因为小娥如果把孩子生下来,不但会影响村里的打算生育工作,而且他们的生活会极度困难。半道士的家景非常贫寒,家里没有像样的炉子,摆设虽然干净,却没几件像样的东西。住在这样的家里,小娥曾通知我,如果没有男友在,她是万万不敢一个人呆着的。可是她自己是没有主张把孩子怎么处理的,男友说了,她要流了孩子,就不要她了。而小娥已经离家出走长达一年之久,家里人为这事已经把她骂过了,也恨过了。我和同事去看小娥一次,她的眼睛红一次。我见过她的他,是个样子还小的男孩子,外表很不错,我想小娥是爱上了他的长相吧,一种单纯而没有理智的爱。
我喜欢往小娥所在的寨子跑,一个原因是因为要做小娥的工作,另一个原因是因为那里盛产美男。除了小娥的男友,寨子里好几个长得极标致的男孩,只是手脚都不太干净,寨中一大户人家的儿子因为偷盗电线,我初进村工作时,就关了出来。
小娥有了转变,是因为在他们预备把唯一的马卖了作营养费的时候,小娥的男友出事了,他步了那个寨上大户人家儿子的后尘,在一个早晨被警察带走了。那个家就剩小娥一人了,没着没落的小娥欲哭无泪,挺着肚子去看了他频频,判下来居然要分离一年多的时间。
一个很冷的早上,小娥自动跑到单位来找我,要求引掉孩子。
孩子引掉并不是很顺利,因为她是第一胎,指导站要求她交三百元意外保证费,小娥预备的营养费却只有二百多元。我事先正处于月底,都没有什么钱了,身上仅有五十元,全数借与她,小娥揣着钱,挺着肚子走了。从那以后,我再都没有见到小娥,不知道事先的她受了如何的苦,但我想一定不会好过。
小娥走过后的那年,我也由村里调回政府,在办公室担任名符其实的秘书一职,再没机会走进那个七零八落的村子了。
阿月离婚了,当我知道这个消息时,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,因为我知道这是迟早的事。阿月的婚姻,死于潜规则。阿月以及她的老公阿飞原来都是某乡村小学老师。阿 ..
无敌战袍 黄昏时分,T国南端的天空出现一个耀眼的火球。 这个奇异的景象自然没有被电视台放过,在黄金时段,电视台播出了这条新闻,并称:"据专家分析,这可能是坠落的卫 ..